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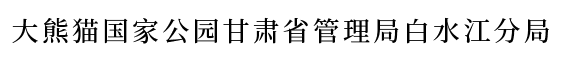
月亮走我也走
在一个寒冷的初夜,我坐在河堤上望月。在无垠的空茫中,我不知道是月亮望着我还是我望着月亮,因为我蓬蓬的羽翅早已折断,而且那种急切情怀宛若河堤之水在脚下汩汩流淌。
路灯照得街面苍白得有些猩红,由近及远,一如星子,渐次坠落在苍茫的月色之中。思维有些天马行空。看月色如水一般泼洒在大地,月容沉积着淡淡的微笑,就像圣女玛利亚,流溢着圣洁的光芒,温暖、安详、肃穆、包容、鸟瞰众生。所有的星子皆沉,所有的光芒皆隐,所有的声音皆寂。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和谐、自然。
自从人类光临月球的那一刻起,美丽的神话似乎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就像你正做着的美梦突然被惊醒,总想这个美梦做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些。其实,永恒的收缩和舒张,永恒的并发和缓解,众人的吸气和呼气,我们正是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运动、存在。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黯然神伤,我们这一代人甚至上上代人,都在古人编织的神话中度过一生。此刻,我更怀念小时候躺在母亲的怀里,望着一轮皓月,听她讲从上代人传承下来的美丽的神话故事,她的语调没有抑扬顿挫,语言朴实舒缓,一如虔诚的信徒,月光照亮了母亲的瞳眸,也照亮了一个普通文化传播者和被传播者的心灵。我幼小的心灵对美好的事物无限神往。但此刻的心情,却极为复杂。
在夜晚,有许多时间可以用来体味人与月亮的关系。亲昵的接纳或冷静的劝诫,温柔的贴近或高傲的远离。月亮是每个人最忠实的朋友,或者,是最美好的情人。它总是含情脉脉地与你对视,接纳你从尘世之中向它诉说的月光,再把月光净化了交还于你。也从不嫌弃我们的不洁或者愚蠢。有时,它还会充当导演,让人们在月光中顺从地去完成一场场情感丰富的表。
记得读高中时,刚学会了骑自行车,便约了同学骑车到一个叫临江的小镇去玩。从学校到小镇约三十公里路程,当时的路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我们兴奋得蹬着脚踏子一路飞奔,一路歌唱,一路欢呼。可惜乐极生悲,在距到达临江的数百米处,车子链条断了,我们不确定小镇上有没有修车的,只好推着车子返回。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走着走着,不觉困顿饥渴,挡了几次车,没有一辆停下来,反倒扬了我们一身灰尘。我们在两边汹涌着的大山合力排挤出的一条生僻仄狭的道路上行走着,天更加黑了。刚转过一个大弯,山顶上突地就出现了一轮颤巍巍的、艳光潋潋的满月,似乎刚刚从大山之间被分娩出来一般。而那些大山终于全部安静了,只沉稳如钢铁材质的剪影般蹲踞。一条汩汩流淌着月光的溪水旁,一片蛙鸣虫奏的乐章里,一潭盛开在山谷内把溪边田地照得如同凌晨般光亮的月光中,我们像漂浮在苍茫的大海中抓到一根浮木,坠入悬崖抓到一根藤条。月亮离黝黑的大山高了一些。又高了一些。虫声啾啾和着蛙声如鼓,一片片皂荚般飘飞入耳,清洗着头脑中的昏沉与困倦,那一刻,所有的一切,包括人,包括机缘,全部为月而生。月亮散发着温暖的光芒,照亮我们回家的路程。
今夜的月色,一如亘古不变的光华,照耀着前世今生,照得白水江像一条闪光的玉带,连接着灯火辉煌的城市。明晃晃的月亮沉在水底,水面闪耀着碎银似的光辉,世界好像已经睡去。如水的月光浇灌我干渴的心灵。吮吸着月光才知道这个夜晚是因为我的努力而生动起来的。我被养育成挺着胸膛的人。站在月亮的高处,我知道明天早晨还有一颗更高的太阳。月亮是我心中缓缓的河流。今夜,我的血液正涌过大地的局部。不然,明天的太阳就不会有青春的气息。我要捞取出我的鲜血一样富有生机的石油,贡献给我热爱的世界,驱动自由的奔腾。终有一天,月亮丰腴了思念的潮。从此,十五的梦不再消瘦。我的血肉之躯重新有了震荡,心与身的关系日渐消失,心与灵却紧紧依偎。你永远是天空的最高点,那一架云梯无止境地延伸。梦幻和神话依赖着黑夜的奥秘,闪耀出一串串光辉。于是我在睡眠中领悟着旷古的奇观。
多少个夜晚,我守着月光的影子,恰似赴着一个遥远而又隐秘的约。月光的影子正是水的影子,那一面易碎的镜,收藏了生命里多少不敢提及的怀想!而今夜的月光变得更轻,它任意地渗进了我骨髓的缝隙,使我几乎忘记了心脏的跳动。我将思想安顿在夜晚中央,一任月光在指间划过---当我这样做时,还有什么不能使我平静地面对?
(责编:一微、冯益华)






 陇ICP备19003004号-1
陇ICP备19003004号-1 陇公安备62122202000128号
陇公安备62122202000128号
